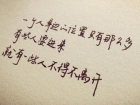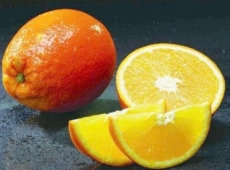即使不提父亲周信芳,周采芹本身也是一个传奇——她是伦敦皇家戏剧学院首位华裔学生(多年后成为该院首位华裔院士);她是1960年代红遍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“身高一米五的炸弹”;她是第一位华裔邦女郎(两次出演《007》电影系列);1970年代做地产生意赔光了所有的积蓄,从昔日的女明星变成弟弟开在洛杉矶的著名Mr.Chow餐馆里的女领班;到保险公司当打字员被告知不胜任这份工作……人生跌到谷底。她一直说“至今还没有教会自己相信命运”,但周采芹的人生还是因为戏剧重回安顿,在波士顿的一个践行“贫困戏剧”理论的职业剧社,度过三年苦行僧般的演员生活。她迷上了表演理论,在塔夫茨大学攻读戏剧硕士,那段求学时光给了她从未有过的“解放”:“我再也不需要东跑西颠才觉得有活力,也不用到谈情说爱中去逃遁躲避”。1981年,受曹禺和金山的邀请,她成为中戏自早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撤走专家以后,第一位到任的“外国”老师,她在课堂上教学生瑜伽却不准他们带纸和笔……1994年,58岁的她叩开了好莱坞的大门——出演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全亚裔主演的电影《喜福会》,轰动全美……上周,为了参加“纪念周信芳诞辰120周年”系列活动,她回到故乡上海。采访中,她思维敏捷、言语犀利。她告诉记者,“我17岁出门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,你要给中国人争气,你要给演员争气,你要给女人争气!现在我快80岁了,我要给老年人争气,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退休。”去年刚拍完《神盾局特工》在内的三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。马上,英国还有一部电影在等着她。

记者:你成为演员,跟父亲有关吗?周采芹:当然有关系,我虽然不是京剧演员,可是我可以拿他的东西来帮助我做西方戏剧。事实上,我爸爸当年也受到很多外国很棒的演员的影响。我新近听到一个笑话,这样说也许要得罪人。我听说中国有三个表演体系:斯坦尼、布莱希特和梅兰芳。戏剧哪有这么简单,要知道布莱希特现在在德国根本就无所谓了。我在教中戏的时候,我一进去大家都拿着笔和纸,在写什么?潜台词。潜台词都可以写成一本小书了,我觉得这是发疯了。演戏是在台上演的,我说你们进我的教室不准带纸和笔,要记得你们的表演是从身体里出来的。我爸爸真正的伟大就在这里,他很早就知道了,包括以丑为美和追求真实。记者:你的书里反复提到60年代,辉煌的伦敦西区的戏剧生涯,还有后来的百老汇。作为一个中国女孩,你是如何征服西方观众的?周采芹:我妈妈最喜欢说英国的一句谚语,Where there’s a will, there is a way(有志者,事竟成)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,再苦也无所谓,因为我年轻啊,而且我没有觉得苦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,我没有被外国人歧视。第一,语言我已经通了,语言不仅是工具,而且是一个战具!尤其是英国人,都很厉害的,你一说话,他马上知道你是什么人了,连出租车司机都是这样的。第二,我是周信芳的女儿,虽然别人不知道,但我自己知道。当年,华裔女演员最吃亏的是找不到好角色,最多就是花瓶。这个就要靠自己慢慢把这片天打下来。我有时同情现在的年轻人,因为技巧可以学到,但是如果演戏的机会不多,演技就出不来,我爸爸也是江湖巡演一路磨练出来的。所以当年我自己就巡演很多,到后来各种观众我完全不怕。要跟最好的演员和导演合作,他们会帮助你越做越好,但在当时这对于华裔演员来说很难。

记者:你也是第一个华裔的邦女郎。周采芹:邦不邦的我根本就无所谓,我最骄傲的是我舞台剧。不过我也理解,因为大家知道的是《007》的电影,舞台剧你们看不到。《007》我拍了两次,我自己两次都没有看过。我对这种戏没有兴趣,但是片酬大得不得了。有时候观众会问,那些好演员,为什么都愿意去好莱坞的电影里演小角色,因为只有赚来钱,他们才能继续维持舞台剧演员的生涯,我也是这样。记者:《喜福会》第一次令好莱坞正视了真实的华裔形象。周采芹:我是好莱坞电影里第一个真实的东方女人形象,这毫不夸张。之前,华人女性只有两种角色,佣人或是三从四德的妇女。男人则不是弱者就是流氓。东方演员长期以来是被压迫的。我是反抗者,虽然代价很大,但我觉得是值得的。记者:你是如何“反抗”的?周采芹:我妈妈告诉我,我是最好的女孩,所以我从来不会低声下气。我第一次在好莱坞演戏,就跟导演说“什么什么不对”,边上很多东方演员就瞪大了眼睛问我说,“我们居然可以跟这么导演说话?”